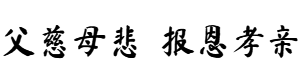東莞五乳犬(來源于《孝犬傳》)
這里說的孝犬,是指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尹家的母犬所生的五條幼犬。(注:陳恭尹,字元孝,著有《獨漉堂集》)
這條母犬身體白色,尾部赤色,四只腳為黑色。陳恭尹為自己的父親死于國難而心中哀痛,立誓不再進入仕途,于是隱居山中,以吟詩飲酒舒發自己的情懷,不與世人交往。這條母犬跟隨著他,片刻不離。每次出門時,它都要走在前面幾百步的地方,像是一名向導。若遇上豺狼蛇虎,它就立刻返回,咬著陳恭尹的衣袂往后拽,不讓他繼續往前走。陳恭尹明白后就轉身返回,這時它又跟在后面數十步遠大聲嗥叫,像是一名護衛。每次出門都這樣,已經習以為常。到了夜里,它就在主人廬舍前后巡視,不時地吠叫,通宵達旦也不休息。
幾年后,這條母犬一次生了五條乳犬,都是公犬。乳犬長大后,陳恭尹把它們分別贈送給前后左右的鄰居家,它們也都能為主人看守門戶,從不懈怠。剛分出去的一年多時間里,母犬每天都去各家探視乳犬一圈,好像是在訓導它們。有了食物,乳犬總是讓母犬先吃。等乳犬長大,母犬便不再前去探視,而幾條乳犬則每天早晨都聚到陳恭尹家,前來看望母犬。
又過了幾年,母犬患上癩病,身體瘦弱,好像就要死去。這幾條乳犬每天都一起趕來,爭著給母犬舐癩,母犬的病竟然好了。每到大年初一,五條乳犬都會一起趕來,繞著母犬搖尾,好像是在為母犬賀歲。后來母犬死了,五條乳犬都哀號不止。陳恭尹憐憫這條母犬,把它埋葬在后山。五條乳犬從此每天早上都一同前去母犬的墓旁哀號,很多年都沒有間斷。
詩曰:
劫火余生笑種瓜,仙厖衛主守煙霞。
不慚獨漉堂前走,孝子鐘靈義士家。
犢吞刀(來源于《柳崖外編》)
沭陽縣有位姓王的屠夫,以殺牛為業。一次,他買下母子兩頭牛,打算先殺母牛,就把它捆起來,磨刀準備宰殺。此時有人敲門,他便放下刀出去。牛犢趁著這個時候銜著刀來到鄰舍孫老漢家門前,用牛角頂門。孫家以種地為業,孫老漢聽到聲音出門一看,見牛犢口里有一把刀,正在往下吞,還剩下一半,不一會兒就全吞了下去,朝著他哀號。孫老漢正為此感到驚異,這時王屠夫因找不到牛犢和刀,也跟了過來。孫老漢問明情況,才知道牛犢之所以吞刀,是不愿母牛遭到宰殺。于是他問明這兩頭牛的價錢,用雙倍的錢買下,然后過去解開母牛,把它牽了過來。牛犢見到母牛便叫起來,一邊叫一邊跪在地上。母牛也在它的旁邊臥下,從頭至尾舔著牛犢。孫老漢原以為牛犢肯定活不了,沒想到過了幾天,竟然沒什么事。
后來,母牛為孫家奮力耕田多年,那頭牛犢則繼續耕種了二十多年,直到孫老漢的兒子那一輩才死。當這頭牛犢死后,有聽說過吞刀奇聞的人剖開它的肚子查看,發現那把刀在腹胃之間,被一層厚皮包著,就像新刀裝在鞘里一樣。
作者柳崖子說:相傳有牛犢為母牛潛埋屠刀,我聽說前些年在家鄉王雅村也發生過類似的事。而這頭牛犢卻為母吞刀,令人倍感酸楚。帶著感恩和依戀,兩頭牛在孫老漢家耕田力作一直到死,可以說母子都沒有辜負救命的深恩。
鶴子點評說:像這樣驚天動地的壯舉,我僅聽說過這么一例。當我在閱讀這個故事時,起初是感到震驚,接著是充滿敬意,接著感動得落淚,接著欣喜地起舞相慶。
詩曰:
吞刀鑿鑿莫疑虛,叩角獨尋孫老廬。
子母乍逢仰天慟,一時狂喜更何如。
孝牛冢(來源于《井蛙錄》)
金溪的前參政官漆尉山,曾對我說:在城南四十里,有個名叫九都的地方。那里有一戶姓黎的農家,養著一頭母牛和它的乳牛,乳牛剛滿半歲。七月間,這位農戶將乳牛拴在家里,駕著母牛在隴上耕作,耕完后把它放到附近的洲渚上吃草。中午時分,忽然烏云翻滾,雷雨大作,母牛竟被雷電擊死。這位姓黎的農戶招集隴上的人,幫忙一起把牛埋葬在河邊。
回家后,見乳牛還臥在牛圈中,不禁心存憐憫,嘆息著說道:“你的母親已經被雷電擊死在隴上的洲渚了。”乳牛聽后忽然站起,悲鳴不已。第二天,農戶牽著乳牛到野外吃草,離洲渚還有一里多,乳牛即飛奔到母牛被雷電擊死的地方,徘徊悲號不止,不吃不喝,怎么趕也不肯走。最后只好用鞭子把它趕回家,到家后它又脫韁逃去。黎家順著印跡尋找,發現它還在母牛被雷擊死的地方,邊繞邊哭,悲鳴聲晝夜不絕,最后撞在地上頭破而死。
鄉里人哀憐它的孝心,便把它埋葬在死的地方,為它建了墳墓,立碑名為“孝牛冢”,至今還在。這是清朝順治丙申年七月發生的事。
詩曰:
膝下初離盼未歸,昨宵含乳夢依依。
英靈尋母河洲遍,怒蹴寒濤十丈飛。